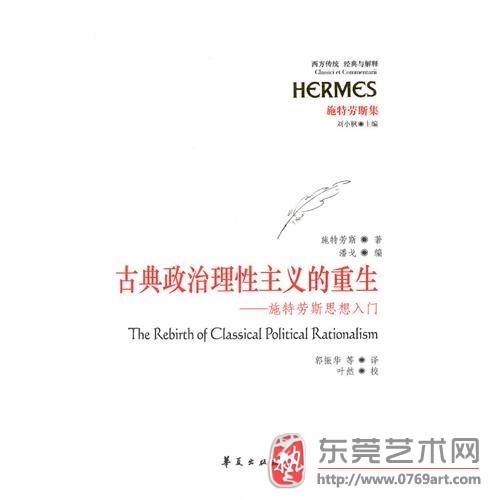
《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施特劳斯思想入门》 [美]列奥·施特劳斯著 郭振华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362页,35.00元
在利奥·施特劳斯所掀起的“复兴古典政治哲学”思潮进入汉语学界整整十年后,施氏本人最具“价值”的论文集之一(根据刘小枫先生之说法)——《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也终于翻译出版了。十年后,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认真检讨的是:施特劳斯究竟给汉语学术写作带来了什么?“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微言大义”的写作体么?
关于通常被称作为“人文-社会科学”(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学问,有两种治学路径:一种是从生活世界人之群处的根本问题出发,从我们的存在性焦灼出发,即从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日常性”出发;另一种则是从学科内某一组抽象的概念、术语或成说出发,通过对它们的疏解与阐释来讨论问题。在当下中国,情形非常鲜明,后一种做法不仅占据压倒性的地位,甚至将自身逻辑展开到极致。学术界里,各种各样的抽象概念、专业术语(terms)、奇门黑话(jargons)铺天盖地,晦涩怪异的书写、句子都被整得不通的行文,却被视作“有学问”的标志。而思想的原初生命,在那些学问里面,一丝也找不到。
施特劳斯主义“古典学研究”2000年左右进入汉语学界后,对这股被刘擎先生称之为“黑话化”的治学风潮之形成,如果不构成主要肇因的话,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之用。至少,事实层面的一个鲜明变化是,不少原本以文笔优美流畅而闻名的作者(如刘小枫),在经历“施特劳斯路标”的转向后,写作的风格也遽变为精心布置的隐微诡异,并以“哲人”、“智慧者”、“知识人”、“卓越者”的精英主义姿态,来睥睨“常人”、“市民”、“庸众”、“老百姓”、“废铜烂铁”……并且,这种神神鬼鬼、精英主义的“微言大义”体,随即很快地席卷学界,对年轻一代学人的写作尤其影响至深。中国式的施特劳斯主义学术研究中,充斥满带炫耀性色彩的拉丁文、古希腊单词;而学术研究本身,已彻底淹没在这些古典术语、各类专学怪词中。
今天,在汉语学界这种主导性治学风格里面,日常生命的向度已然隐匿不见。那些怪词满溢的“黑话式写作”,不经几层“转译”,或者专业性的“解码”,社会公众——中国施特劳斯主义者们笔下的“常人”、“庸众”、“废铜烂铁”——根本无从读通。学者的研究亦不复涵有日常遭遇中的反复运思、一日三省,而是直接从学科内某一组抽象的概念或既有的争论出发,进行经院性的疏解或批驳。
然而,我不得不追问的是:汉语施特劳斯主义者们所引领的这股治学风格的转向,是否真的得施特劳斯之真义?施翁到底为什么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之所以向往古典的政治哲人,正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存在一个政治哲学的传统。而之后所有的时代中,哲人们关于政治事物的研究,就在那个政治哲学传统的规介下进行——它就像是夹在哲人与政治事物之间的一个屏风,不管个体哲人对那个传统予以珍视抑或加以拒斥。这就进一步引出如下论题:古典哲人们,以一种鲜活性(freshness)和直接性(directness)来检视政治事物,此后一直没有达到过那种鲜活性与直接性的程度。他们从受教育的公民或政治家的视角来看政治事物。他们将公民或政治家们没有看清,或根本没有看到的事物,看得很清晰。但这不是因为其他缘故,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从一个相同于公民或政治家的方向去看,但比后者看得更深更远。他们并不从外部来看政治事物,像是政治生活的观察者那样。他们以公民或政治家的语言进行论说:他们极少使用哪怕一个对于公共生活而言不熟悉的术语……和古典政治哲学相比,所有后面的政治思想,尤其是现代政治思想,具有一个派生性的性格(无论它还具有其它什么的特点)。这意味着,在后面的时代中发生了这样一个状况:对朴素和原初的问题的一个疏远。这个状况,就给予了政治哲学‘抽象性’的性格”。 更具体地说,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承袭性的知识(inherited knowledge)构成,这样的知识之基础不再是同代性的(contemporaneous),抑或,它是无法直接进入的(immediately accessible)。”与之相对,“古典政治哲学里没有哲学史”,“无论历史性的知识对于政治哲学有多重要,它都只是预备性的和辅助性的,它并不构成政治哲学固有的部分”。因此,施氏宣称:“对于那种所必需有的政治哲学的真正理解,也许只有以把所有传统都抖落掉的方式,才能成为可能;我们时代的危机,也许恰恰带来这样一个意外的好处——使我们能够以一种非传统的、或鲜活的方式,去理解那些以前只是以一种传统的或派生性的方式被理解的东西。”如果说古代政治哲人是真正的思想者(thinker)的话,那么现代政治哲人至多只是“学者”(scholar),“学者通过书本的中介而面对诸种根本的问题,如果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尝试以伟大书本作为中介。而伟大的思想者们直接面对问题”。施特劳斯指出,“学者”之所以能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思想者们的观点彼此有差异,甚至异议。“学者”认为自己可以站在历史的后端来检视那些以前的思想,对它们做出评判。然而即使这个工作,施氏强调,也是基于一种盲目的自负,基于对历史“进步”的信仰上。今天学术的那种“专业化”、“学科化”,在施氏看来,就是“对少之又少的事情知道的多而又多”(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
之所以引述施特劳斯以上论点,就是旨在指出:在施氏眼里,所谓古代人的学问和现代人的学问的真正区别,就在于古代人直接在生活世界里,以“鲜活性”和“直接性”来讨论问题。思想的原初活力在哪里?施特劳斯主义的答案是:它就在人们的每日遭逢中,就是在苏格拉底式追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虔诚、什么是高贵、什么是节制、什么是疯狂、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懦弱、什么是根基、什么是城邦、什么是政治家、什么是统治等等中;同样地,就是在樊迟问知、颜渊问仁、孟武伯问孝、子贡问君子、林放问礼之本、季康子问政等等中……换言之,思想实践的源头,就是在生活/生命的日常遭遇之中,就是在人与人如何群处、如何互动的各类问题中。而现代人不再以那种方式来做学问,他们直接从来自过往文本的“承袭性的知识”开始,用概念讨论概念。在那样一个闭合的短路里面,生活世界、日常生命彻底排除在外。他们的用语、行文,根本不是公共生活里的阅读大众能读懂。人话说得像鬼话,还以为这就是学问之深奥;必须要神神鬼鬼,非如此不显出智慧者的高贵……
对这种盛行于当下汉语学界的治学风格,施特劳斯的批评恰恰是很有洞见的:他从休谟这里借来“感受”(impressions)一词,以指代那种“第一手的体验”(first-hand experience)。他举例,“城”(city)的理念,就是从我们对城市的直接感受中出来,就如同“狗”的理念来自我们对狗的直接感受。而对“国家”(state)这个理念,我们就无法拥有任何的直接感受或体验。换言之,它是“概念生概念”生出来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国内引介施特劳斯的主事者们,在他们关于施氏的引介文字中,以及《施特劳斯集》各中译本中,一律将其The City and Man译为《城邦与人》。这便恰恰说明了,他们尚未彻底读通施特劳斯。“city”不是“city-state”,后者是属于历史的,属于古希腊。千百年后“城邦”早已不复存在,甚至哪天“国家”的概念也可能不复存在,但“城”仍然会在,它是——对施特劳斯而言——自然的。故此,“城邦”不能与“人”对,而“城”可以与“人”对。《城与人》,被画蛇添足成了《城邦与人》,从这个“足”上便可看出这些自认施特劳斯东方传人的神神鬼鬼的水平。
因此,对施特劳斯而言,存在着两类完全不同的理念。对于前一种直接扎根在日常感受与体验中的理念(如“狗”、“城”),我们在生活世界里就可以直接体触到它的同代性;但要研究后一种理念(如“国家”、“主权”),我们就只有一头扎进学术史的过往文献中进行专学式的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研究。然而,问题就在于:如施氏所言,“抽象没有问题,但对根本性的东西进行抽象,就有很大的问题。”
施特劳斯对“古典理性主义”的复兴,在思想意旨的层面,系胡塞尔、海德格尔两人的发展,旨在拆去各种抽象术语、专学黑话所编织起的藩篱,使学术研究重新返回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世界。对施氏而言,被各种知识传统、专业术语所支配的“现代性状况”,乃是一个“洞穴下的陷坑”(pit beneath the cave),或者说“第二洞穴”。施特劳斯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主张就是:我们必须首先回到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即回到习俗上的生活世界——公民与政治家的日常实践(即古希腊的nomos),然后再是“苏格拉底式的上升”——以哲学化的方式上升到真理的阳光下(即physis,自然)。是以,我们必须驯服承袭性的知识,去让前述的后一种理念(学院化的抽象概念)变回第一种理念(生活世界里的符号),重新恢复它们的鲜活性和直接性。换言之,在治学路径上,我们必须把现代性的专学变回古典的通学,将铺天盖地的术语和黑话,变回生命性的遭逢与触通;不然,做出来的只能是似是而非的假学问,而非“真知”。
今天汉语学界的许多学者,为什么要写得如此艰涩、远离“常人”,如此术语带术语、从概念到概念呢?我无法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伪)精英主义的姿态,固然是不少自我宣称的“智慧者们”选择这种学术写作风格的一个原因,好在种种神神鬼鬼的话语包装内、半通不通的拉丁文-古希腊语的充门面下,将自己与“庸众”、“常人”拉开一个话语性-象征性的距离(discursive-symbolic distance)。然而,另外一种现象,亦是同这种学术写作大为兴盛密切相关。在这里只举一个晚近的例子。
最近这段时间“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大热,拥护者们一路说过来皆好似很有学问,也给了你很多专业数据、专门名词……但你听完后回家,怎么感觉都不对劲。因为它和你自己的“第一手的体验”、生活世界的“感受”完全对不起来。你随便上一下网、和朋友或出租司机聊个天,完全不对啊。于是,从施特劳斯古典视角出发,值得追问的正是:如果我们都能以古典政治哲人之鲜活性和直接性来做学问,汉语思想界的“纷争”还会那么大么?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和判断,真的连一点共识也达不成么?大家都生活在里面,谁也不要糊弄谁。但一加上术语、黑话,专业学术包装、抽象概念里一打转,那就不对了。不要说黑猫白猫,狗也可以变成猫。中国以前有个大太监,为了检视一下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而组织了一场指鹿为马的剧场实验。今天那些学者权力当然没有那么大,可以这么玩,但通过他们“专业性”的研究一转换,用海派清口的话说,周扒皮进去,周立波出来,白猫黑猫塞进去,“中国模式”流出来……
可见,专业化的晦涩高深、术语套术语、概念生概念的写作有多重要。也正因此,我们需要严肃地去追随施特劳斯的号召,即,返回古典政治哲人的治学实践——日常现实的向度,怎可在学术研究中抽去?研究“中国问题”,有必要如施特劳斯所强调的,“返回到公民的视角”,“像有思想的、思路开阔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理解社会现实那样地去理解社会现实”。确实,研究者们有可能看得比一般公民们更远,但必须从他们相同的方向去看。学术的研究必须——至少在起点处——和公民们的关注相关,和生活世界里的人们的存在性焦灼相关。研究者们必须使用——或学会使用——公民们的语言来讨论问题。这,才是施特劳斯召唤“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之真义。
在施特劳斯进入中国十年之际,在那神神鬼鬼的所谓“施特劳斯体”业已成为汉语学界主导性的治学风格的当下时刻,我们不得不去严肃地重新思索,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原初意旨。如果我们旨在真正追随施特劳斯的教导的话(而不是狐假虎威式地借施氏以自命精英),我们就有必要去让学术研究重新和我们的生活世界、日常生命相通;我们有必要在进行“学者”的研究的同时,也像古典哲人、真正的思想者那样,直接走向“政治哲学”本身;我们有必要努力使自己从那“派生性”的抽象研究,返回到学术研究的原初状态中,去重新恢复思想实践的那份鲜活性和直接性。质言之,古典性的“重生”,就是去使承袭性的“知识”,变成为生命性的“学问”。






